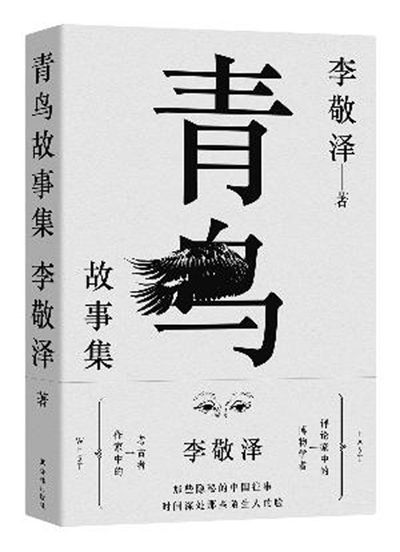
这本书,你最好夜读。万物俱静,心神合一之时,你所有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,追逐着自书中缓缓逸出的香,感受它精妙复杂的美与奥义。你能闻到清少纳言“枯了的葵叶,雏祭的器具,绸绢碎片”,能闻到李贺的“袅袅沉水烟”和让宋徽宗神魂颠倒的“龙涎香”,那从久远历史散发出来的沉香萦绕着你,让你心醉神迷,渺思万里。但是,且慢,这不只是一部感性之书,它让你着迷,但不会让你沉迷。你当然会被书中的清雅和精妙所吸引,它们的来路太过奇特,好像你从来不曾感知,你更被吸引并为之着迷的是它们被编织的方式,在语言的往返缠绕和对那一缕香、一朵玫瑰、一本奏章的执着追寻之中,生活和历史的另外镜像被呈现出来。
这是一本书中之书,是一次关于知识的再建构。《博物志》《太平广记》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《太平御览》《中国基督徒史》《中国之欧洲》《旧中国杂记》……时间倒流,那被遗忘了的长安,已经坍塌的街道房屋,已成尘埃的裙裾、瓦罐再次恢复,世界重又细致入微、栩栩如生。
时间再次开始。李敬泽把知识解放出来,变为活的纹理,重新编织我们的生活。看似闲话野史,边角废料,却恰恰勾勒出历史形成的另类逻辑。你可以说它是知识考古,文中所涉奏章、杂书、公文、诗句,都严密可靠,有谱系学的意味,但是,依靠作者高超的想象力,所谓的“物”与“知识”不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物和科学意义上的知识。就像艾柯的《玫瑰之名》和卡尔维诺《宇宙奇趣》,以“物”起始,却不止于物。它集中于对“物”所包含的人类心性、历史和象征进行考察,在物的世界内部,牢牢贴附着人的精神需求,因此,“玫瑰”与“蔷薇”的混淆不是简单的错认,而是一次漫长的跨文化旅行。
所以,初看《青鸟故事集》,感觉非常传统,古雅、玄妙,承继中国文学“文”的传统,远有《春秋》《庄子》作底色,又不乏搜神志怪、笔记体之神韵,也颇具唐宋传奇之气场,当然也有现代文学时期随笔式散文的恣肆,譬如梁遇春的《春醪集》,纵横捭阖,旁征博引,意趣横生。细细品味,却又都不尽相同。它的旨意不只在表达文学趣味和人生的某种况味,考古不只是为了考古,博物不只是打捞风物,它指向更宽阔的面向。
李敬泽要重新起高楼,创空间,注气息。他要把游离于历史之外的、已经遗失于时间黑洞之中的书、物和人再次拉回,让我们重新发现世界。叙事和修辞不只是技巧,它就是世界本身,是审美,也是意义。本雅明最大的梦想是“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”,博尔赫斯许多小说都以他人的故事为故事,他们都致力于完成一个巨大的野心:让知识重新成为生活,并赋予世界以新的意义和形象。所以,你完全可以说《青鸟故事集》是一部小说(不管是随笔小说、考古小说还是侦探小说等等之类)。李敬泽就像一位穿行于“交叉小径花园”的间谍,根据一个模糊暧昧的线索,甚或,只是一句“袅袅沉水烟”,跳入时空迷宫和浩瀚文献中,奋不顾身,又乐在其中。
阅读这部书,你经常会迷失于其浩大空间和奇异想象中,但是在某一瞬间,几个知识点突然撞击,火花四溅,遥远不相干的时空和身体连接起来,产生了艾略特所说的“化合作用”,碎片变为整体的一部分,并从陈腐化为生机。一切都豁然开朗。于是,唐代元稹的诗与马戛尔尼使团中的那个“李子神父”之间发生了联系,1947年的开罗会议和《旧中国杂记》中的那个案件有了同质性,它们都是“返与他心腹”“翻来诱同族”。“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”,近代历史上的“鸦片战争”不只是教科书中告诉我们的那些结论式的话语,那个错误百出的、经由无数次“鸟译”而面目全非的奏章有可能才是故事的最大主角。
何为青鸟?报信之人。语言是其基本的媒介,它的任务是要传达真实。但是,正如柏拉图著名的“洞穴”理论,人们会把自己的影像当作真实。而语言,则是关于影像的描述,是影子的影子,是产生误解的根本原由。
误解,其实就是误读。误读是世界形成的根本。《飞鸟的谱系》就是一次关于误读的叙事。它的故事主干来自于美国人威廉·亨特《旧中国杂记》中所写的一个案件。印度水手在中国广州犯案,法官请来英国人老汤姆作翻译,老汤姆又请来会说几句印度话的木匠翻译阿树,于是,几个人进行了一场“驴唇不对马嘴”的对话,法官在审讯,阿树在推销自家私货,印度水手则一头雾水,旁边一群洞若观火的人在围观。这个场景非常具有隐喻性。语言在人群上空乱飞,没有达成任何交流。但,这就是交流。正如作者所言,“语言的相遇是两种互不交融的‘现实’的碰撞,只有他们能够将双方引入同一个现实平面。”而“历史就这样在多种多样的想象和幻觉的冲突中展开”。这正是16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相遇时的基本状况。
东方、西方,各自携带着关于远方的想象,或者说相互歪曲,并在歪曲和谬误中产生新的结果和意义。“那棵银树也是一面有着神奇魔力的双面镜子,东方和西方、中国和欧洲,在镜子的两边相互凝望。”“镜中之相”,这既是近代中国在世界中的形象,也是我们理解自身的原点。从来就不存在孤绝的文化,我们身处镜像之中,互为他者,在镜像中窥探世界,也想象自我。在互为镜像的焦虑、误解和碰撞中,我们失去自我,或者是建构新的自我。
在这一意义上,李敬泽就是那只殷勤的“青鸟”,怀着对语言和生活的热爱,探看历史的幽深处,因为,他坚信,“历史的面貌、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”,在那里,有我们遗失了的自由的身体和真实的形象。


